文/赵健
本文来源/公众号“嘤鸣读书会”
电影《挖掘机》截屏
在一个施工现场,
挖掘机挖出了几具尸骨,
司机惊讶的发现,
这些就是二十年前“光州事件”中被镇压的人,
而他自己当年则是参与镇压的一名军人。
挖掘机司机抱着骷髅头哭泣
从此他开着破旧的挖掘机,
去寻找当年的战友,
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
师团长、司令官、甚至找到了总统,
他问了每个人同一个问题:
“当年为什么派我们去那里?”
这就是刚上映的韩国电影《挖掘机》的故事,风靡一时的《出租车司机》并没有盖过这部片子的光芒,在韩国的影评网站上,普遍给出了比《出租车司机》更高的评分。
《出租车司机》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勾起了一个国家的共同记忆,甚至还启发了其他某些国家的无限联想。而《挖掘机》则聚焦了光州事件中的“那一小撮人”——那些开枪的士兵,谴责他们、憎恨他们、同情他们、悲悯他们。
《出租车司机》展现了极权统治下人性的挣扎与反抗,而《挖掘机》更为残忍地揭露了公众道德的冷漠,那些缺乏良知勇气的观望、退却、陈腐。
更为重要的,《出租车司机》是一部商业片,而《挖掘机》是一部独立电影。其实我个人对“独立电影”原本并不抱太多期望,因为我们在赞扬独立电影时,往往不是因为它拍的画面和内容有多好,而是因为它制作过程的辛苦和不容易,尤其是中国的一些独立电影,情怀往往超过了内容,人们在看到它制作并不精良的画面时,想想“毕竟这是独立电影”也就宽容对待了。
但《挖掘机》是一部兼具思想与美学的优秀独立电影。
《挖掘机》的画面很“唯美”,甚至比很多商业片还更干净、更纯净,但美的画面里是无处不在的残酷与暴力,这种鲜明而又强烈的反差感,使画面更有视觉冲击、带来更大的内心震撼。影片中甚至很少用到配乐,只是简短而有力的台词,与其说是在看一部电影,倒不如说是在听一场振聋发聩、直至歇斯底里的演讲。
人性本善吗?
人性可以变善吗?
善良,能否成为成为一种抗拒罪恶的力量?
《挖掘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挖掘机》很像一种希区柯克式的悬念设置,主人公一直在问每个人同一个问题:“你当初为什么要派我们去那里?”每个人都说是来自上级的命令,从普通士兵、团长、师长、大将、一直追问到总统。难道这是总统一个人的错吗?这么大的历史事件,仅靠一个人就能救赎吗?
想起先前读过的某位作家,回到自己家乡后,发现了对面坐着的一位老人正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当年抄家时对父亲拳打脚踢甚至抽鞭子,但时隔境迁,这个“恶人”已成为眼前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他曾无数次幻想过当自己见到这个“恶人”后一定会上去拳脚报复,但他看了这位垂垂老朽的老人,突然没有了报复的动力,只能无奈地慨叹:“时间已经在惩罚他了”。
有些罪恶是很难惩罚的,却又是不能宽恕的。
《挖掘机》展现这些军人的另一面生活,展现了他们退伍后生活得多么艰辛与挣扎,并不是为他们辩解,也不是认为他们当年的罪恶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可以被原谅的。消解了犯罪动机的恶,依然是一种恶。
如果说《出租车司机》一幕悲壮的现实主义作品,那《挖掘机》则是一种“半抽象电影”,导演在努力地呈现世界的本体,这是一种克里斯蒂安说的“社会总体事实”。
那些开枪的士兵,其实只是冰山露出来的一角,至于淹没在海平面以下的部分,很少有人关注,他们当初为什么选择开枪?他们当时内心在想什么?他们后悔吗?他们后来过得怎么样?这就是荣格所概括的“集体潜意识”。
汉娜阿伦特在面对德国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时候,发现这个犯罪者令人震惊的“平庸”,如此“陈词滥调”,丝毫没有一个主动犯罪者应该具有的深刻的罪恶意图。这是一种“平庸的恶”。艾希曼只是一个尽职完成上级命令的普通军人,尽管他在纳粹体系中扮演这一个杀人机器。但是当时的法官宣布,尽管开枪杀人可能并不是你的动机,尽管不是你来执行也会换做别人来,但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
无论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军人艾希曼,还是《挖掘机》中光州事件里开枪的士兵们,他们都是一个犯下弥天大罪的犯罪者,同时又是一个尽责的父亲、丈夫和一个恪尽职守的公务员,甚至还是某个领域里的“好人”。他们脱下军装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他们有父母、有妻儿、有艺术爱好、追求爱情、追求自由与幸福,但他们穿上军装就成了刽子手,用子弹、鞭子、毒气等手段折磨敌人和同胞、折磨那些手无寸铁的父亲、妻子和婴儿。正是在生活方式的惰性中的正常与面对极端道德决策事件中的良知拷问,一个平庸的人显现了出来。这正是平庸之恶的可怕之处!
这是一个人们在理智上能认同,但在情感上很难接受的事实:
当反对的声音、人道的声音被封杀,个别人的恶与疯狂又迎合了多数人的弱点,就可能迅速变成群体性的恶与疯狂。比极权统治更可怕的,是杀人的执行者、配合者、默许者的群体的心安理得与麻木不仁,他们不觉得是在做一件错误的事情,而是在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不可选择的事。
他们已经准备好和其他人做一样的事——包括告密、批斗、杀人,甚至大屠杀。也许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是无奈的、合法的、不会被惩罚的、不会被宣布有罪的,但是在这种看似道德中立的、合法的纵容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
每个看似正常的无思想的普通公民的心里可能都潜藏着一个罪恶的刽子手,如果不能看到这种追究的本质,整个人类将会排队出现在战犯被告席上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一个官员,不把自己当做是一个人,而只是把自己当做是某一个体制中的工具和小齿轮,当他犯了历史的罪行就可以被免责,那么,所有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官职的人,都可以用同样的借口去犯罪而免受历史的惩罚。
主人公当年故意把子弹射在“莫名其妙的地方”
《出租车司机》是那个时代的反抗者,
而《挖掘机》揭露的则是沉默的大多数。
但为什么有些人能够选择“不从众”,甚至不认同、不执行?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质疑。而这种质疑,源于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辨的能力,能让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狂时依然保持一种清醒的判断力。
司机开着挖掘机冲向总统府官邸
挖掘机上写着“为什么派我们去那里”
优秀的民族,始终不曾停止对自己的反思和鞭挞。
我羡慕韩国能有《挖掘机》这样的电影,不用含沙射影,不用考虑审查制度,而是坦坦荡荡地追问曾经的错误。
《挖掘机》超越《出租车司机》的地方在于,它超越了自身的民族身份、公共体制、意识形态等等,重新去追问真相,也为真相的多元化提供了一个例子。
看完影片我自然地想到了《圣经》里有个故事:法利赛人捉住了一位正在行淫的妇人去刁难耶稣,妇人的行为依摩西律当乱石砸死。耶稣如果不处死妇人,便犯了违律罪;若处死妇人,则又犯了杀人罪。看似两难的问题耶稣只用一句话就轻松化解: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砸她。围观众人闻听此话,纷纷离去,作鸟兽散了。为什么没人敢说自己无罪呢?这大概就是西方人的“原罪”意识,而这种原罪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会让所有人都陷入绝望,进退两难的绝望、内心纠缠的绝望。
司机把白骨掩埋后立起十字架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其实有些到今天也还相信。就比如《挖掘机》里的主人公,他不知疲倦地追问每个人同一个问题,无一例外地被赶了出来,他就像希腊神话里的那位西西弗斯,永无休止推着石头上山,尽管这石头注定要再一次滚下来。
就比如我明知写这样的文章有风险,但依然选择表达,是因为我坚信,没有什么能逃过时间的审判,很多这个时代的“常识”和“真理”,会在下个时代被我们的后人所推翻和鄙视。我们不能靠掩藏起丑恶来为世人制造一种虚假的美。
作为“这一代”里普通的一个年轻人,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在我们面前,逝去的是几代人的理想,留下的是让人哑口无言的“理想”破碎后扎脚的碎片。如何迈出脚步,走过刺痛、危险又别无选择的荒野抵达新的理想,并提醒自己要时时小心它重蹈覆辙,这是不知道又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征途。
講述韓國軍政府血腥鎮壓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事件的韓片「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大陸翻譯片名為「出租車司機」),8月上映後不久,北京網信辦下令,查刪所有相關介紹、百科、影評、推薦等文章。目前該片在大陸各大搜尋、電影、新聞網站以及微博的相關訊息幾已全遭下架。
《出租車司機》由真人真事改編,講述1980年韓國時任總統全鬥煥暴力鎮壓光州學生民主運動的故事。主人公金萬夑是一名出租車司機,從不願關心政治,不贊同學生爭取民主,到為了掙錢,拉德國記者到光州,之後親眼目睹光州的警察軍人開槍鎮壓大學生和市民,明白真相後的金萬夑協助記者拍下真實的影像,成功帶出光州昭告於世。
該電影背景與講述的故事與28年前的北京「六四」事件很相似,由此引發大陸民眾共鳴,也觸動了中共的敏感神經。
筆者則想到了另外一部同樣以光州事件為角度的韓國電影——《挖掘機》。 《挖掘機》在韓國的影評網站上,民眾普遍給出了比《出租車司機》更高的評價。
如果說《出租車司機》引起了觀眾對那段歷史的回憶,那麼《挖掘機》則聚焦了光州事件中的最需要一個國家共同反思的——那些開槍的士兵。如果說《出租車司機》展現的是極權統治下人性的反抗與掙扎,而《挖掘機》則揭露了人性道德的集體冷漠。
該片以光州事件退役戒嚴軍兵長的視角,講述了該事件後20年,既是加害者又是被害者的鎮壓軍人們的生活,及該事件帶給人們的後續影響。 《出租車司機》是呈現的是悲壯的現實主義,《挖掘機》則不斷的拷問我們的良知。
《挖掘機》是一部兼備思想與美學的獨立電影。影片中甚至很少用到配樂,只是簡短有力的台詞,令觀眾直接聽到看到的,是一場振聾發聵演講,直指人心。影片裡的主人公,幾乎一直在追問每個當初的加害者與被害者,同一個問題:「你當初為什麼要派我們去那裡?」每個人都幾乎無奈的說是來自上級的命令,從普通士兵、團長、師長、大將、一直追問到總統。 這麼大的歷史事件,真的難道只是總統一個人的錯?當泯滅人性的罪惡得以橫行,吹滅良知的,是一個人的噤聲,還是所有人的噤聲?
影片中那些開槍的士兵,其實只是冰山的一角,而沉在海平面以下的部分,又有多少被人們關注?他們當初為什麼選擇開槍?他們當時內心在想什麼?他們後來有無後悔?他們所做的事情,包括那些告密、批鬥、殺人,甚至大屠殺,在當時的環境下,也許他們的藉口是無奈、怕會被懲罰、或者覺得不會被判有罪,但是在這種看似道德中立、合法的縱容中, 沒有一個人可以最終在道義中得到原諒。
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作者)面對艾希曼,發現這個罪犯表現出來的,令人震驚的「平庸」,好像艾希曼只是一個盡職完成上級命令的普通軍人,儘管他在納粹體系中扮演這一個殺人機器。但是當時的法官宣佈,艾希曼殺人行經絕不是平庸,是罪惡。
無論是希特勒統治下的軍人艾希曼,還是《挖掘機》中光州事件里開槍的士兵們,他們都是一個個犯下彌天大罪的犯罪者,同時,他們又是一個盡責的父親、丈夫和一個恪盡職守的公務員,甚至還是某個領域里的「好人」。 他們有父母、有妻兒、 追求自由與幸福,但是,你能說這些脫下軍裝後和正常人沒什麼區別的, 用子彈、鞭子、毒氣等殘忍手段折磨自己同胞、折磨那些手無寸鐵的父親、妻子和嬰兒的,不是劊子手嗎? 有些罪惡可以通過懲罰,然而有些罪惡,已經超越了世間倫理, 會拷問我們每個人的一生。導演在劇中直接拷問的,正是每個人的道義良知。
當惡魔的瘋狂脅迫了人性的的弱點,當反對者的聲音得不到回應而遭到封殺, 比極權統治更可怕的,正是那些執行者、配合者、默許者的群體麻木不仁。良知在那時候,閉上了眼睛,吹滅內心道義呼喊的,不是囂張的邪惡,正是我們每個人的一片沈默。
每個普通公民的心裡可能都潛藏著一個罪惡的劊子手。只需要在那些「由一小撮犯罪者」行惡時保持沈默。 如果一個官員,不把自己首先當做是一個人,而只是把自己當做是某一個體制中的工具,以為犯了罪行就可以被免責,如果人人都這麼想,那麼,將來恐怕整個人類會排隊出現在歷史的被告席上 。對罪惡的沈默即是同罪。
然而,仍然有些人能夠選擇不認同、不執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性中對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質疑。而這種質疑,源於良知的思考能力。這種獨立思辨的能力,能讓一個人在整個國家都陷入瘋狂時依然保持著清醒。
優秀的民族,始終不曾停止對歷史的反思。《挖掘機》是這樣的電影,用直接坦蕩的追問指出曾經的錯誤。
沒有什麼能逃過時間的最終審判。面對大是大非,永遠不要閉上良知的雙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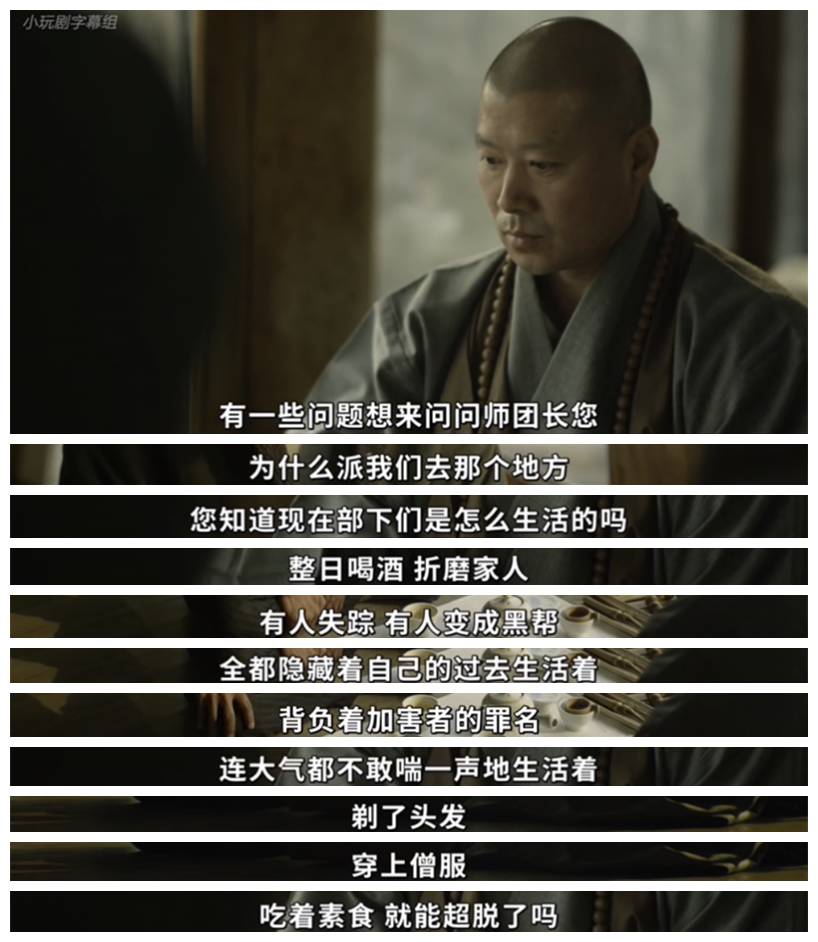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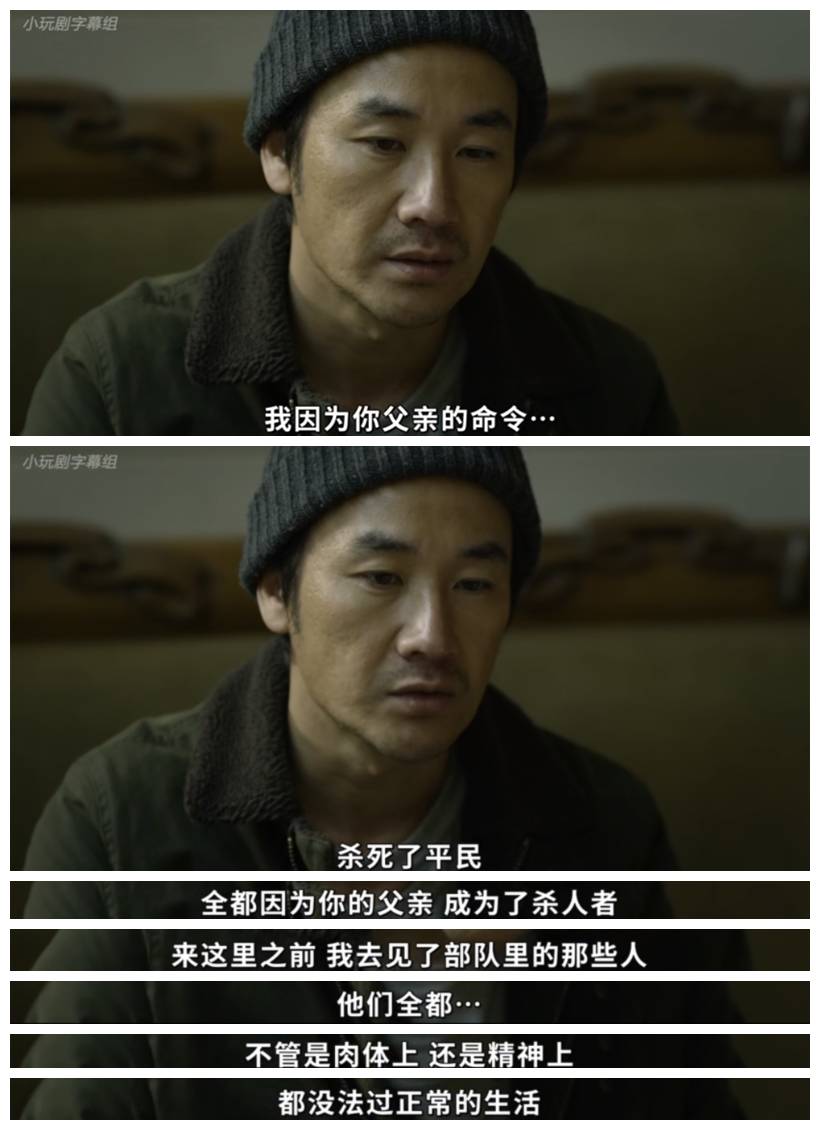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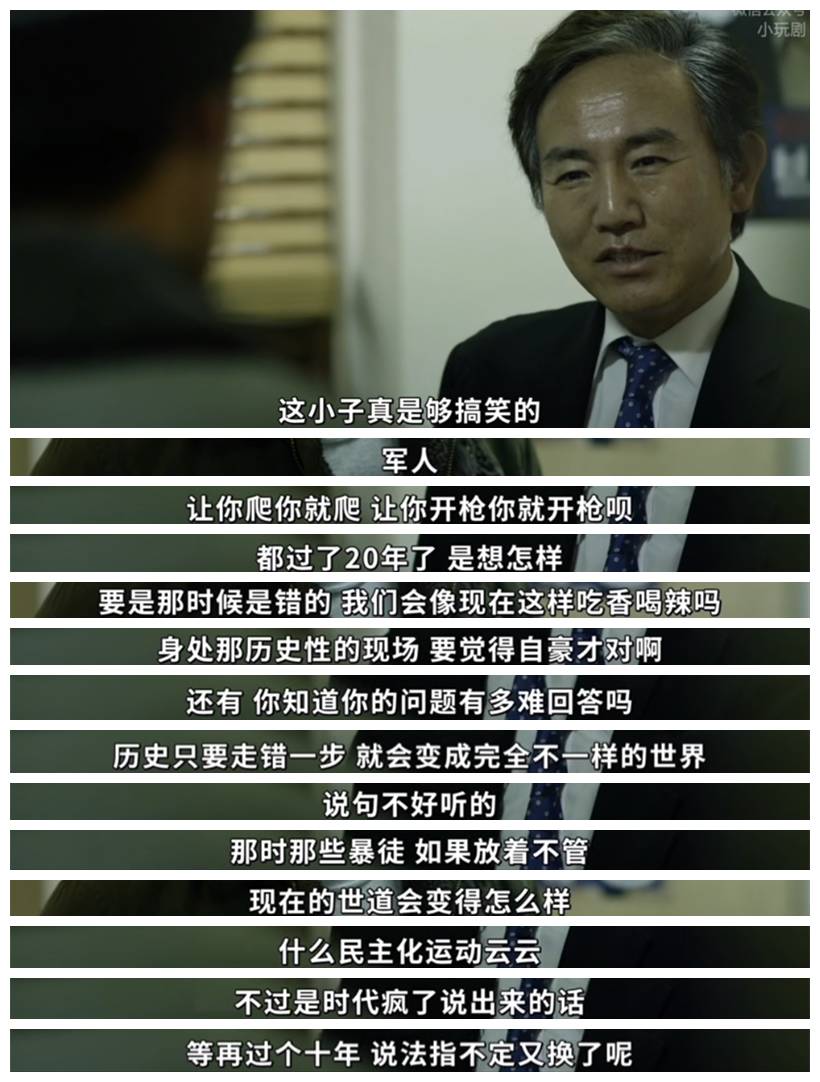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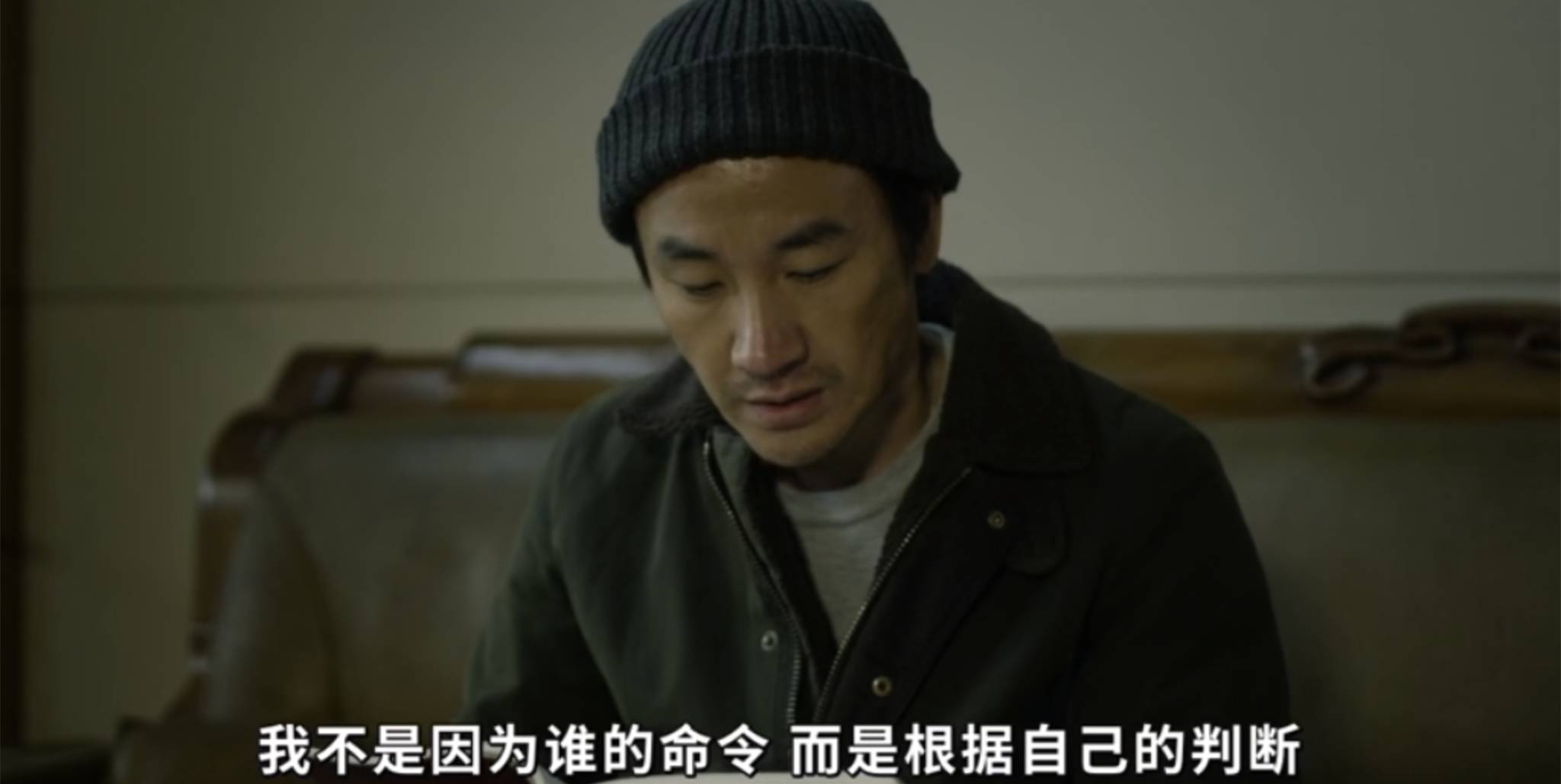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